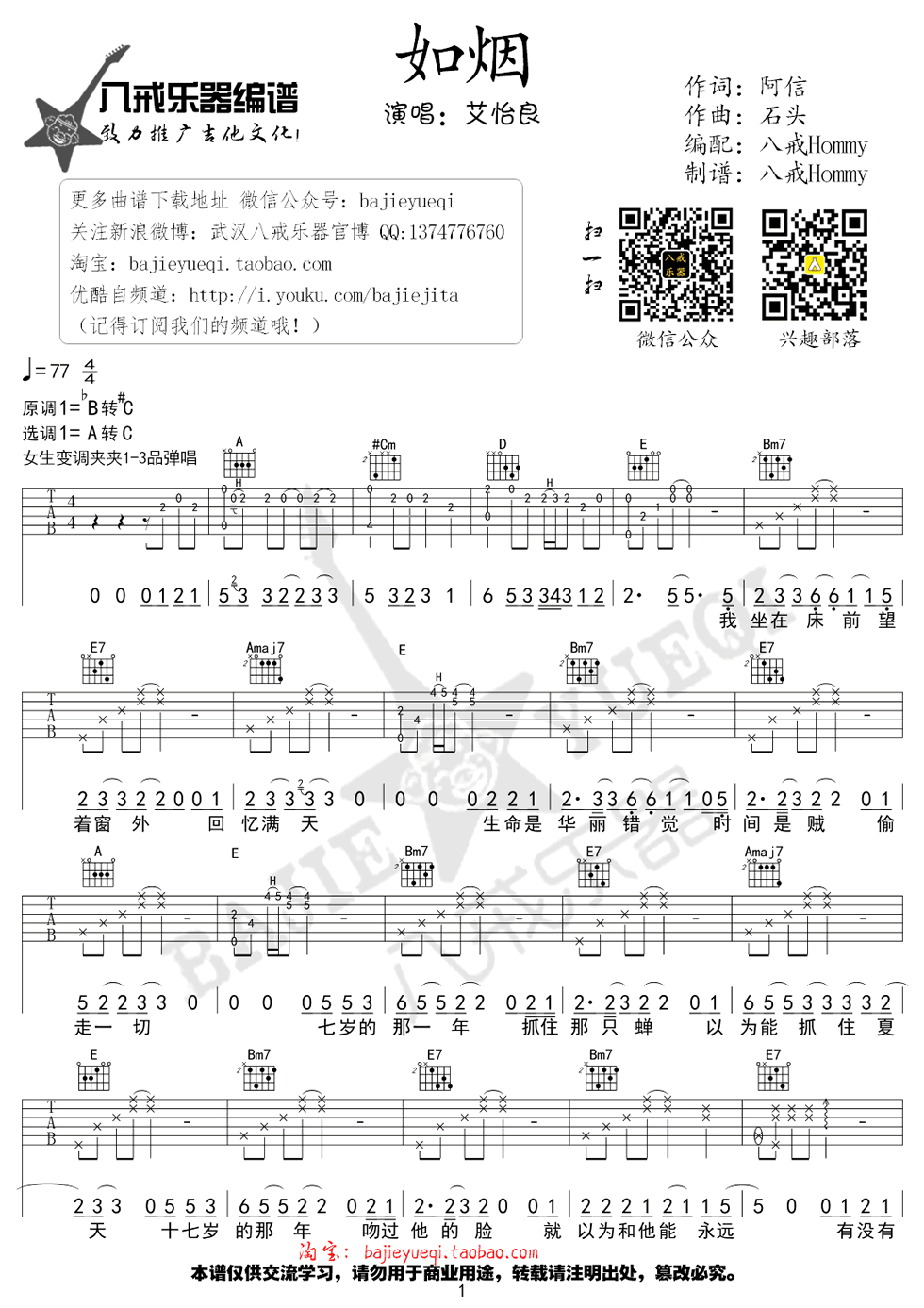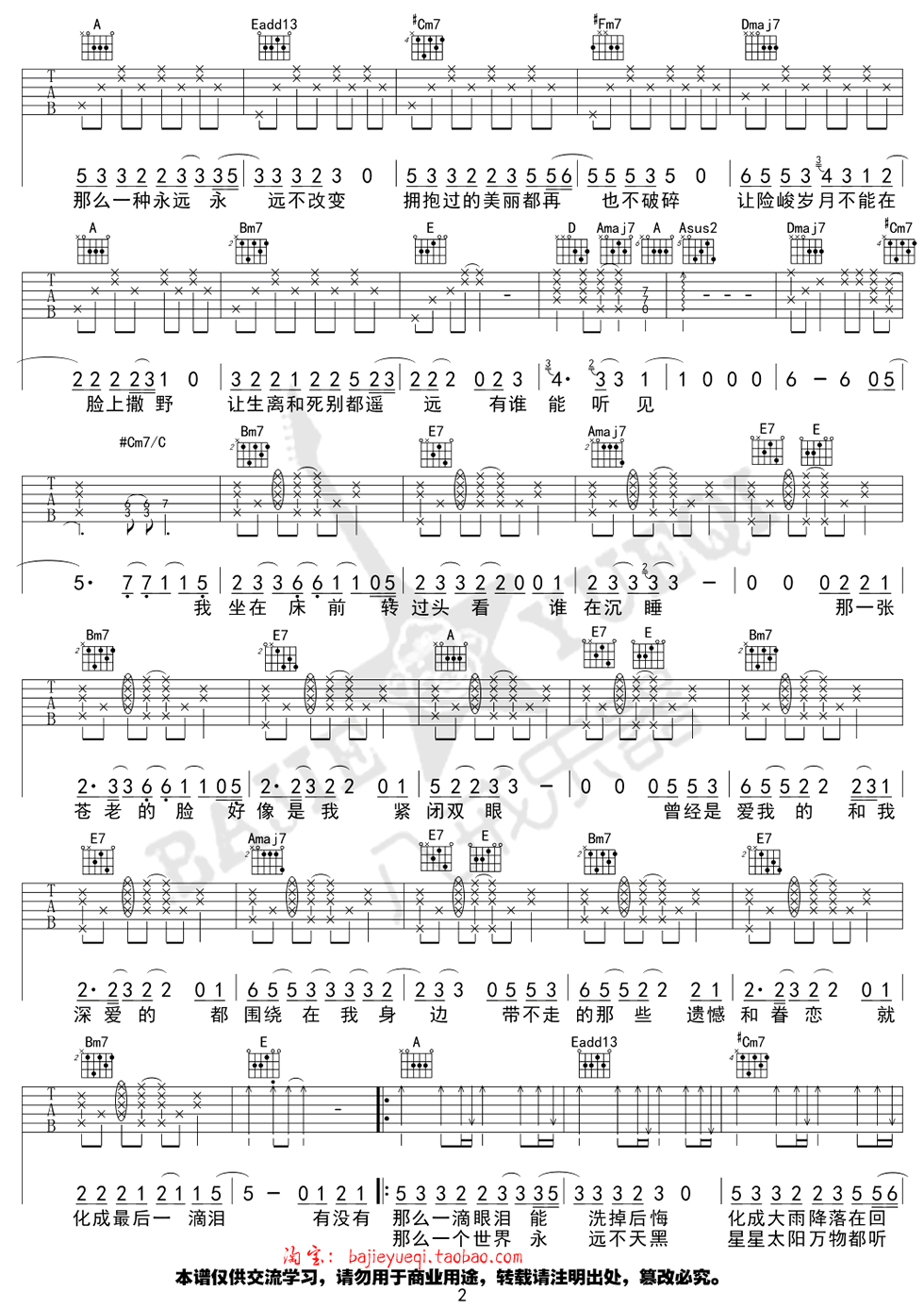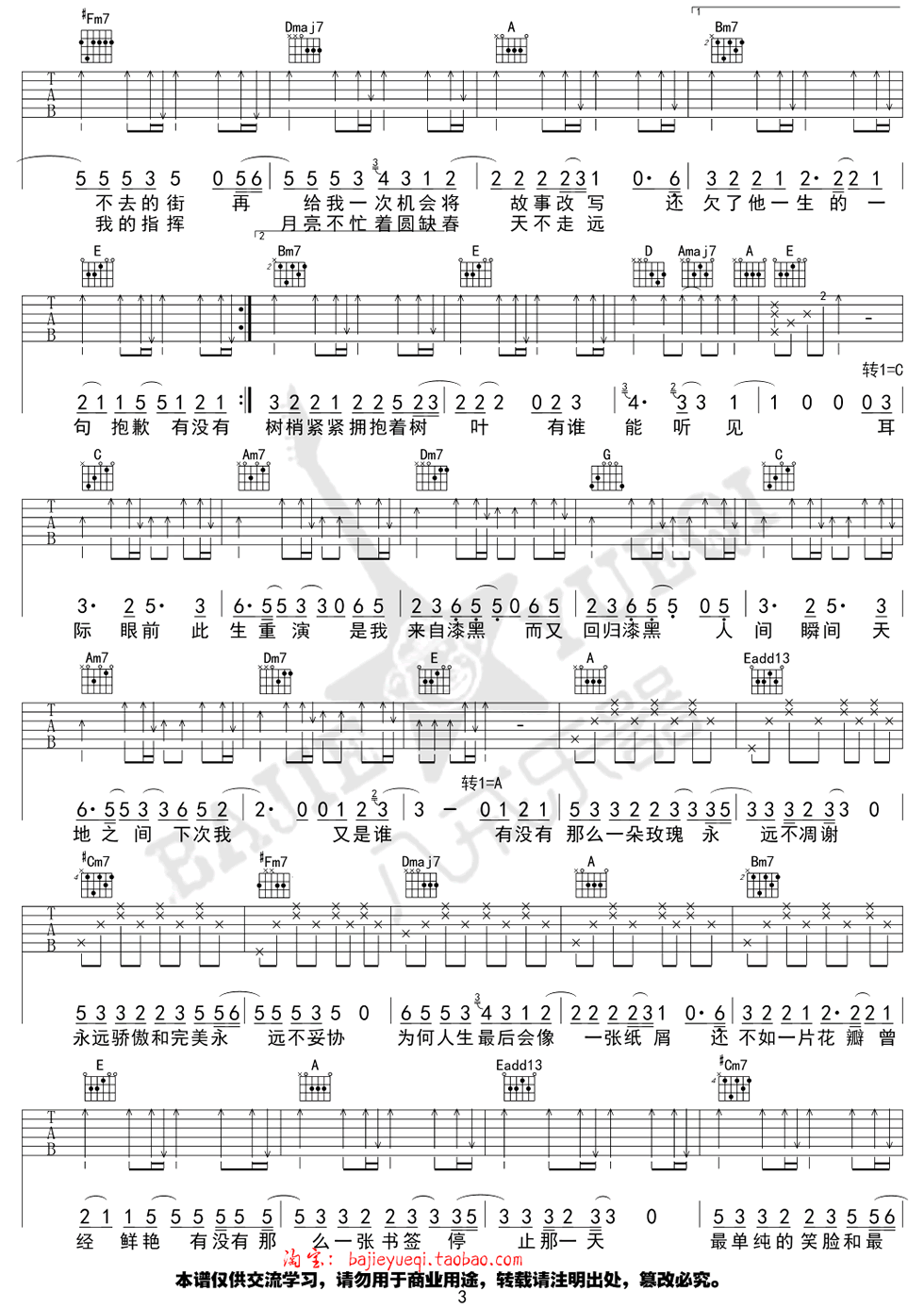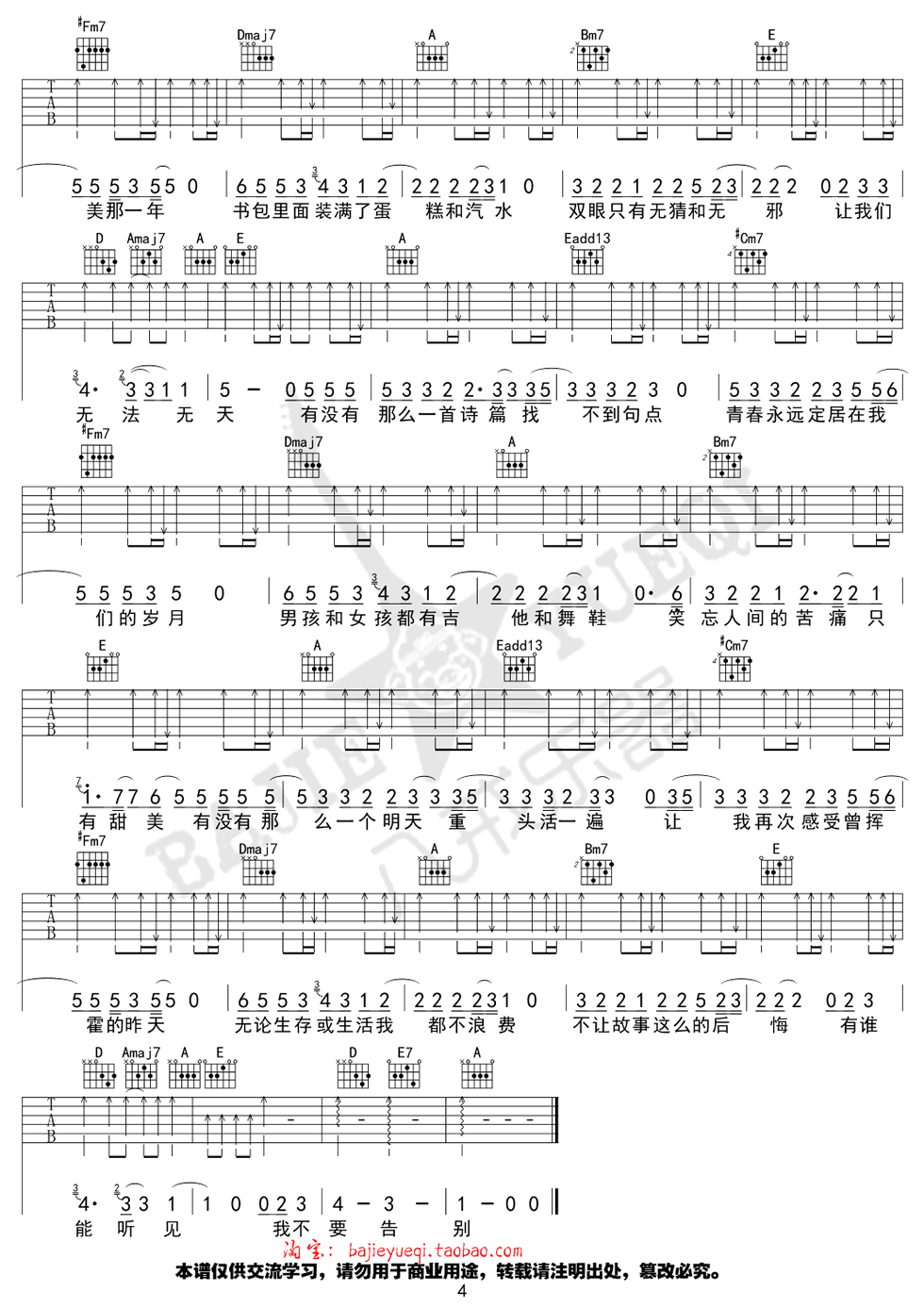《如烟》以飘渺的意象勾勒出时光易逝与记忆褪色的怅惘,通过烟雾的物理特性隐喻情感的不可捉摸与生命的无常轨迹。歌词中“指尖缠绕的雾气”与“旧相框里的侧脸”形成虚实交错的双重意象,既描绘物理层面的消散过程,又暗示情感记忆在时间长河中的模糊变形。贯穿全篇的“风”作为不可抗力的象征,既加速烟雾的离散,也推动叙事向前,暗示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性。灰烬与星火的辩证关系构成核心隐喻,燃烧后的残留物与未熄的余温并存,恰如生命中逝去的与尚存的情感羁绊。城市霓虹与薄雾的视觉对比强化了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感,在喧嚣中愈发清晰的孤独被具象化为“渐渐透明的誓言”。结尾处“未写完的信笺”作为开放式意象,既保留对过往的追忆可能,也承认了叙事本身的不完整性,这种留白手法将抒情主体从具体故事中抽离,使歌词获得超越个人经验的普适共鸣。全篇通过细腻的物象转换,完成对存在主义命题的诗意表达——所有热烈终将冷却,但消散过程本身构成了存在的证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