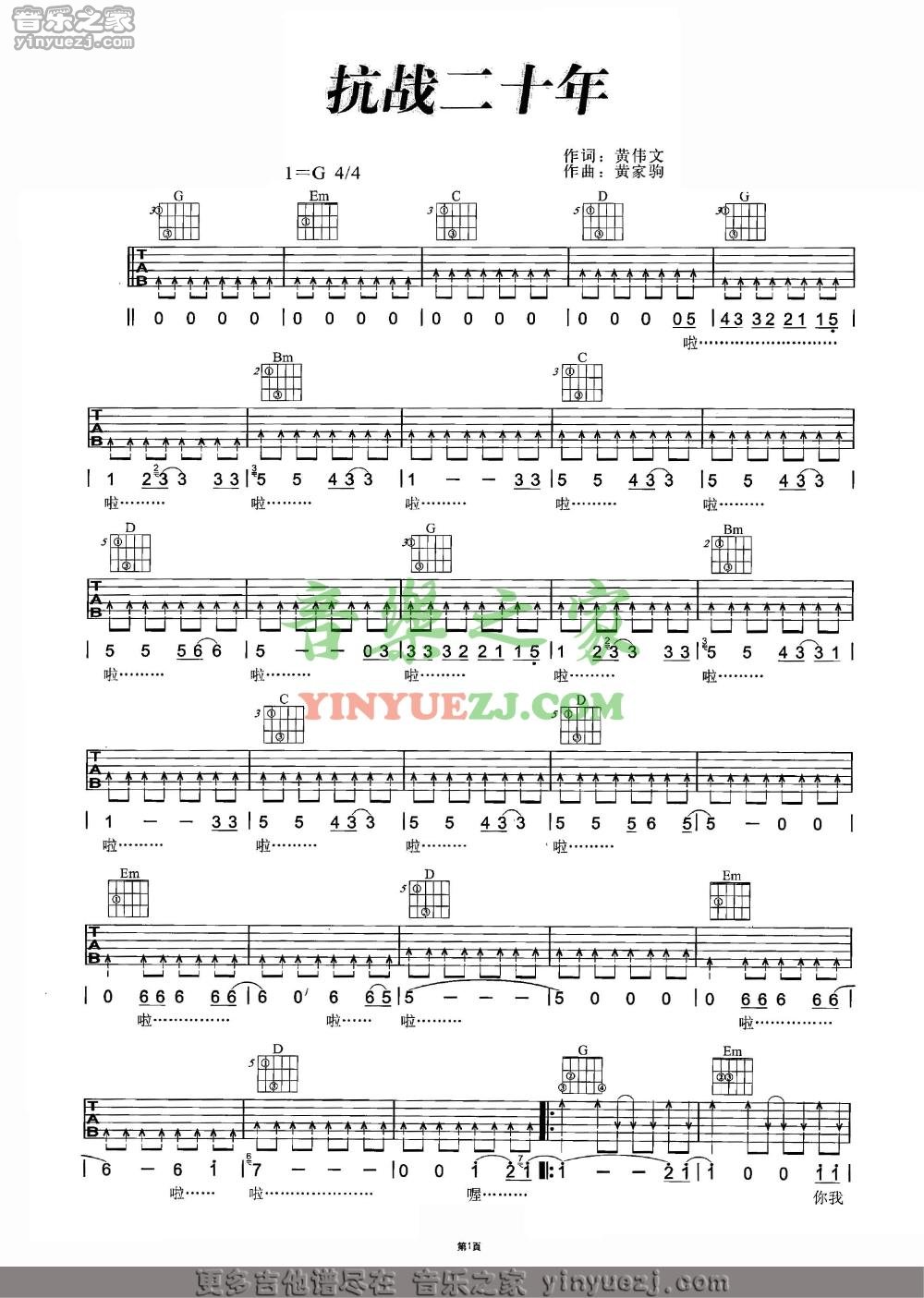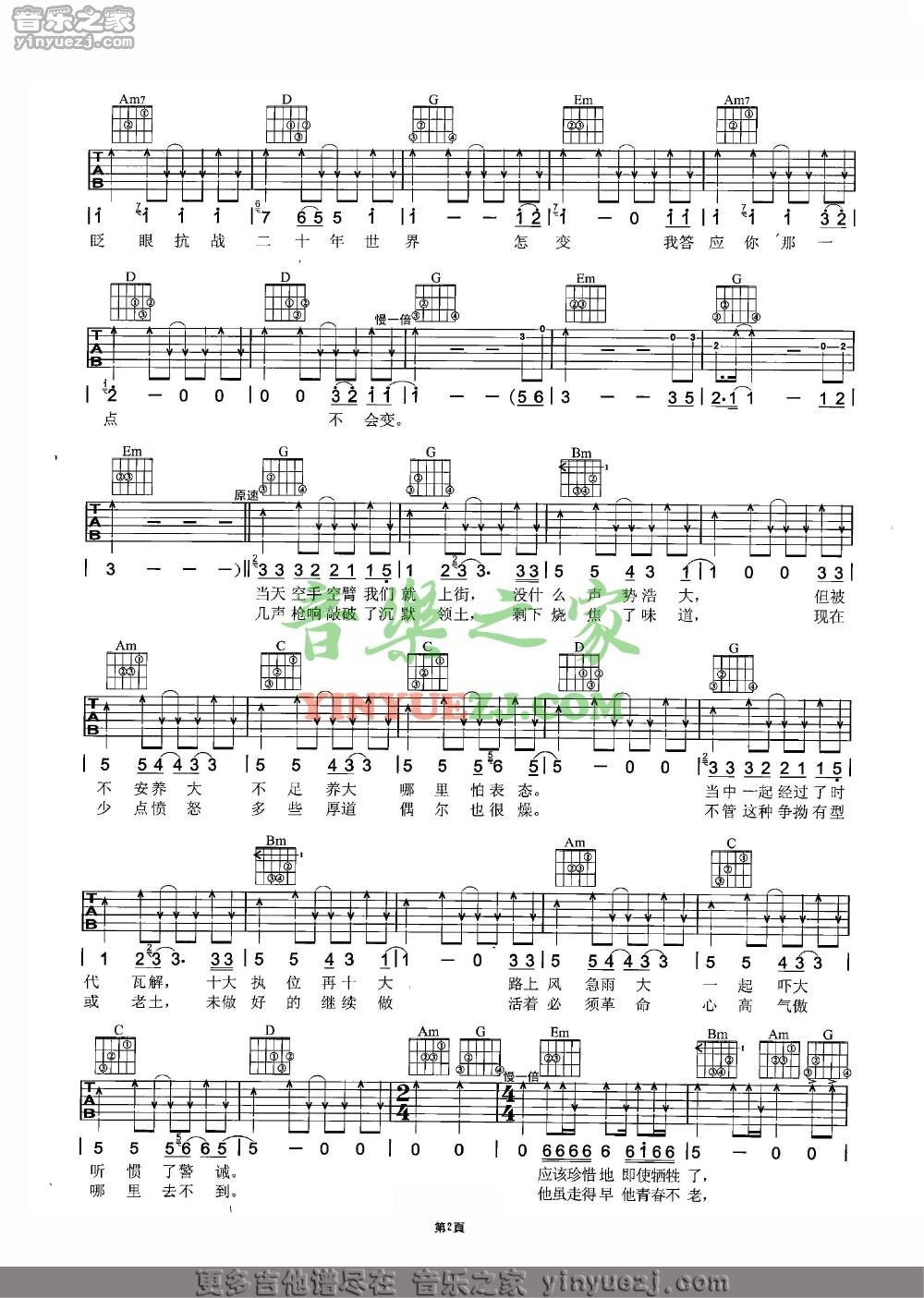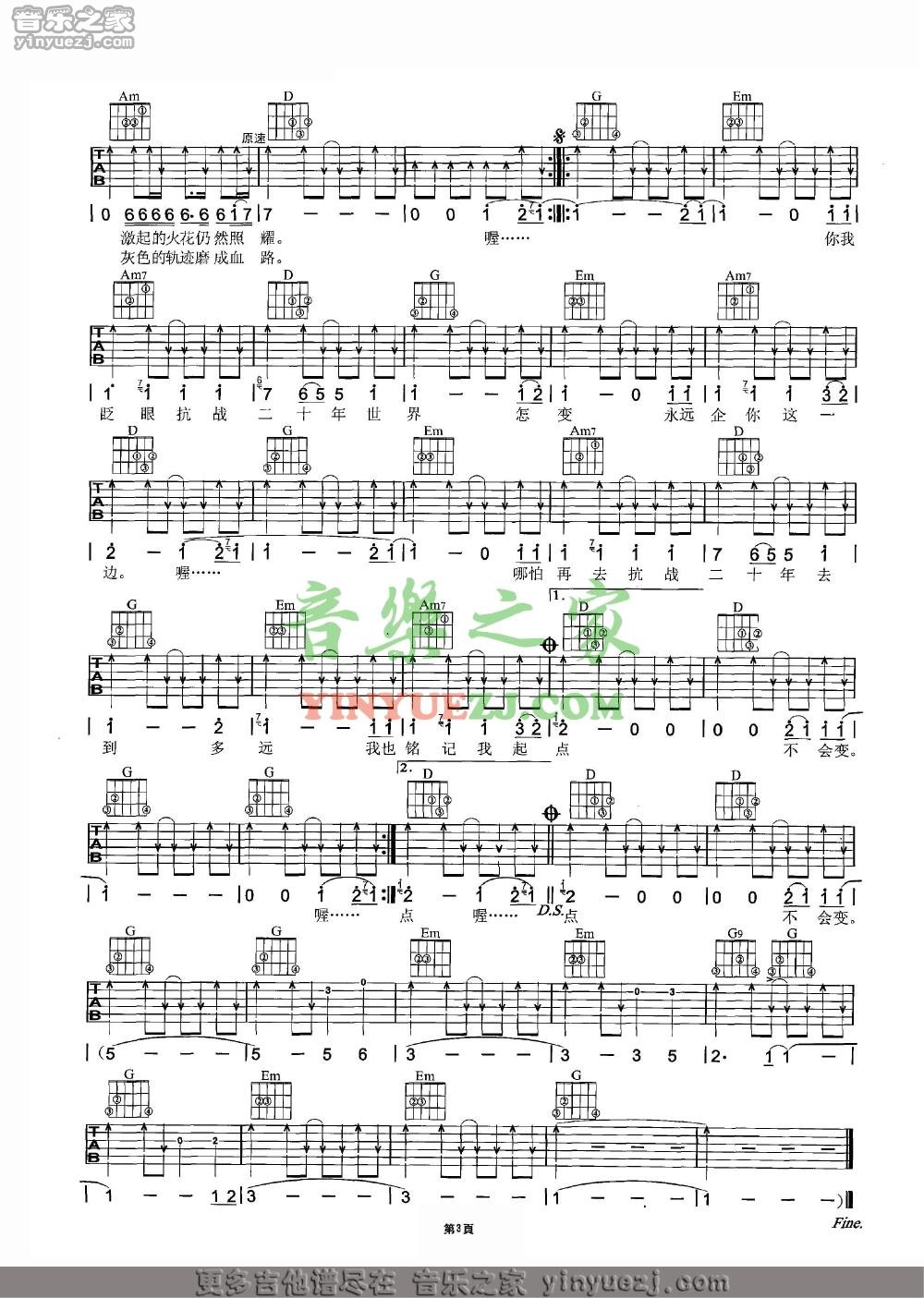《抗战二十年》以深沉而克制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民族抗争的漫长画卷,歌词中绵延的时间刻度与具象的意象群像形成双重叙事。硝烟与麦浪的意象并置暗示着战争对农耕文明的撕裂,母亲纺车与父亲镐头在炮火中的变形,成为普通家庭被时代洪流裹挟的隐喻。二十个寒暑的轮回不仅指向物理时间的累积,更暗喻抗争精神在代际间的传递,月光下磨刀的场景与黎明前吹号的声音构成动静相生的抗争美学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长路"意象既是地理上的迁徙轨迹,也是民族命运的精神投射,鞋底渗血的细节将宏大叙事落实到个体生命的痛感体验。山河与墓碑的互文关系揭示记忆载体的双重性,幸存者眼角的皱纹里沉积的不仅是岁月,更是历史见证的沉重。炊烟在废墟上的每一次升起都是对毁灭的无声抗争,童谣与战歌的交替传唱形成文化韧性的复调。最终落在未熄灭的火种意象,暗示抗争精神超越具体战争形态的永恒价值,在时间的淬炼中升华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底色。